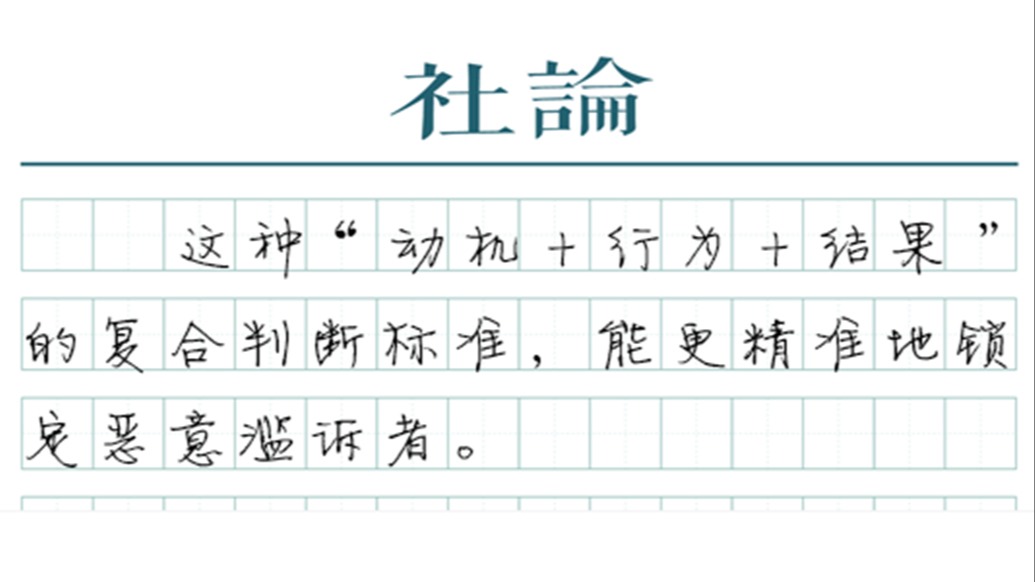
11月19日,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加强诚信建设治理恶意诉讼工作纪实》和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,向全社会传递出鲜明信号:司法既要为正当维权撑腰,更要对“诉讼式碰瓷”亮剑。
现实中,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“暗箭”时有显现。某公司在上市关键期,突然遭金某公司的专利诉讼,诉讼的爆发时间颇具“针对性”。法院查明,金某公司在起诉前,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评价报告告知“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”。明知专利权利基础不稳定,金某公司却刻意隐匿该报告,最终被法院认定并非正当维权,而是意在拖延对方的上市进程,构成恶意诉讼。
在另一起专利侵权纠纷中,同样也是在对方公司上市的关键期提起的诉讼(之后撤诉),但法院认为,“不能简单以诉讼的不利结果推定起诉人具有恶意”,意在确立恶意诉讼认定的“审慎与谦抑”原则。
有的案件认定为恶意诉讼,有的案件又不予认定,看似矛盾的审理结果,其实指向一致,就是精准划定“诉讼式碰瓷”的治理边界:既要依法打击故意利用诉讼谋取不当利益者,也要保护公众正当合理的诉讼权利。
司法乃社会之公器。知识产权领域的恶意诉讼之所以成为公害,在于其以合法形式行非法目的,将诉讼异化为打击竞争对手的工具。这不仅扰乱市场秩序、挫伤创新动力,更消解司法权威。
在民事诉讼法中,明确对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,通过诉讼、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,“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,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”。有了法律条文仅是前提,更难的在于,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判定恶意诉讼。
这一次,最高法典型案例给出了治理恶意诉讼的破题思路。针对金某公司案,法院提炼出四大“恶意表征”:专利本身不具备授权条件、隐匿不利评价报告、索赔金额显著失衡、起诉时机精准狙击上市——这些多维度的“恶意拼图”,构成了认定恶意诉讼的关键坐标。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了核心认定要件:诉讼缺乏权利基础或事实依据、起诉人主观明知、造成实际损害、行为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。这种“动机+行为+结果”的复合判断标准,能更精准地锁定恶意滥诉者。
面对“诉讼式碰瓷”,法院既要以法律为准绳,坚守“审慎与谦抑”的裁判品格,避免“宁可错杀”的激进,也要通过细化标准,让恶意诉讼无处遁形。







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